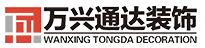
優(yōu)秀設計師
從記事兒起,爺爺、大伯、二伯、三伯、五伯就常招呼一幫戲迷朋友來家唱京戲。我們這一大家子人都愛唱戲,都能演幾出折子戲,雖不及專業(yè)出身,但都樂在其中。時常,業(yè)余戲迷朋友來我二伯家一唱就是小一天。唱得差不多時,三伯掌勺的燉菜也做熟了。吃飽喝足后,爺爺?shù)木┖懫穑鹆恕抖ㄜ娚健贰N乙矊W著二伯的架勢比劃著,逗得旁人哈哈大笑。
待戲迷們都回家了,爺爺、大伯、二伯閑下來問我:“喜歡唱戲嗎?”“喜歡!”“想學嗎?”我睜大了眼睛,頻頻點頭。二伯說:“那就給你講講戲。學戲要認真,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wǎng)。”接著,他唱一句,我便跟著唱起來。爺爺聽后笑著說:“還真有那么點味啊!”就這樣,戲曲的韻慢慢地在我幼小的心里扎了根。

爺爺十七歲時在北京前門我姑奶奶的裁縫店里做學徒,白天學手藝,晚上去看戲。他最喜歡看馬連良的戲,拔得多高的調(diào)門兒都看不到馬連良一點用力的樣子,真叫一個享受!學徒?jīng)]兩三年,爺爺就去了北京市被服廠。他肯吃苦,技術好,一天能做八件棉襖。掙的錢,爺爺幾乎全花在看戲上。有一次早報上登著梅蘭芳要連演四天,爺爺吃了午飯,騎著車子就去買票,誰知四天的戲票全部售罄。爺爺不死心,天天在門口轉(zhuǎn)悠。到第四天時,他看到報上登著“今晚加演一場《宇宙鋒》”,把爺爺美的,立刻騎上車去買票。那是他第一次看梅蘭芳的戲。還有許多京劇大家,如李少春、葉盛蘭、蓋叫天、譚富英、金少山、楊寶森……他們的戲爺爺都看過,不僅記得戲,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票價。
我會唱的好幾段老生戲都是爺爺、二伯教的,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家店》。當時,二伯把音頻資料用磁帶錄好拿給我。拿回家后,我趴在大錄音機旁反復琢磨每一個“過門”。那時候,爸媽給我買的京劇磁帶、光盤,我真是翻來覆去地聽。戲?qū)W會了,就難免生出表演的想法,總想登臺亮相,那才能真正過過戲癮。
快到年根兒,二伯開始招呼村里年輕力壯的小伙兒到村口學校對面的大操場搭戲臺子。戲臺子一旦搭起來,會一直從正月初二唱到正月十五之后。有好幾箱子的行頭,要拿出來掛好。有大伯、二伯合作《武家坡》《游龍戲鳳》《坐宮》時穿的,還有大伯唱《玉堂春》時穿的。舞臺比較簡陋,木板子搭的臺子,支上鐵架子,用布把臺子左右兩側(cè)和后面罩起來,正面的臺子上方貼著爺爺用大紅紙寫的“林城京劇專場”六字。好幾個兩百瓦的大燈泡在戲臺上下掛起,亮亮堂堂。村民們熱情高漲,翹首以待大年初二的到來。不管天氣多冷、雪積得多厚,只要戲臺上的鑼鼓點響起,大操場上準是人山人海、喝彩迭起。
大部分節(jié)目都是彩唱,清唱的劇目一般放到前頭。我演第一個節(jié)目:《打龍袍》。唱完,就見二伯帶著妝早在后臺等著了。他火急火燎地拉著我快步走,一邊夸我唱得好,一邊趕緊帶我到化妝臺,給我扮上鐵鏡公主丫頭的妝容。大伯飾演男旦鐵鏡公主。在好幾個兩百瓦的大燈泡的照耀下,大伯頭上的配飾金光閃閃。二伯飾演的楊四郎目若朗星、挺拔精神,引得臺下叫好不斷。一身身五顏六色的簇新行頭,讓戲臺上一時間繽紛奪目、光彩照人。二伯和大伯一唱一和的流水板,臺下的鄉(xiāng)親們都聽得入迷。此刻,勞作了一年的鄉(xiāng)親們,伴著一浪高過一浪的歡呼喝彩聲,沉浸在正月的喜慶和歡樂中……
《 人民日報 》( 2022年08月20日 08 版)。推薦閱讀: